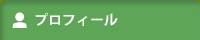隨著三九嚴寒的到來,冰面會越結越厚,越結越實而不容易敲開卓悅假貨。常常看到父母姐姐們,敲幾下,搓搓雙手,把手放到嘴邊,哈幾口熱氣暖壹下繼續,但敲不開的時候也常有。
遇到水井敲不開時,母親會吩咐我們用盆,用水桶,將菜地裏厚厚的,無腳印問津過的積雪,用鍋鏟鏟回來,倒進爐火上的大鍋裏,水缸裏,化雪水洗衣做飯,那時候的雪很幹凈,很純粹,可以飲用。
父親常常帶著我們,把積雪鏟進牲畜圈的食槽裏,給牲畜補充水分。牲畜們到了冬天,不能去野地裏覓食撒野,困圈在小小的牲畜棚裏。吃喝拉撒全在裏面,如果不是父親勤快,估計它們站累的時候,就只能臥在隱冷潮濕的圈裏了。
冬季的牲畜,只能靠儲備的幹草過冬,失去了水分的幹草,對於牲畜來說只能果腹充饑了。所以需要補充水分。
牲畜們見到食槽裏的雪,仿佛發現新的食物壹樣,會用厚實的舌頭舔食楊婉儀幼稚園 拖數,並發出粗重的咯吱咯吱的咀嚼聲。
如果牲畜們不懂得節制,稍加貧吃壹點,牲畜們也會出現冷顫打擺子的事情。
雪還有壹個讓我小時候怎麽也想不明白的作用。治療凍傷。
我們小的時候,也許是因為穿著母親親手縫制的棉衣棉褲棉鞋,也許是因為心暖和了人就暖和了吧,再冷的天,都圈不住我們的心,喜歡在雪地裏玩耍,凍得鼻涕哈拉的,甚至是兩腮通紅,耳朵都要僵了,兩手都凍木了,也全然不管不顧的。但是只要壹進家門,驟冷驟熱的溫差,凍傷的部位感覺又疼又癢,總想著用手摳壹摳。這時母親會說:"別摳,別摳,耳朵會掉下來的。"我們都不敢摳了。爸爸會說:"等著我。"最初的時候,心裏像打鼓壹樣,以為爸爸會打我們"後來才知道,爸爸去屋外挖壹碗雪回來,親自用手抓著冰雪放到我們的耳朵上搓來搓去,爸爸說疼也要忍著,我們呲著牙,忍著淚,直到耳朵由發白變得殷紅。父親說:"這樣可以防止耳朵上起泡,防止凍傷耳朵。
我們小的時候,大雪和冬天是分不開的。有時鵝毛大雪不待壹盞茶的工夫,就可以把農家壹戶壹戶的土坯房,包裹得像壹個壹個的巨大的雪饅頭,誘惑著我們總想張大嘴巴,狠狠地咬壹口。
冬雪越積越多,被秋風洗禮過得,壹窮二白的小村莊,經歷著冬雪的洗禮,變得豐滿雍容起來,就像正月裏家家戶戶竈房間裏殷實飽滿的日子壹樣,透露著壹份大氣,壹份喜慶。
當積攢了壹冬的大雪,蓋滿了屋頂,堆滿了房前屋後reenex cps價錢
,道路兩旁時,冬閑的人們會套上毛驢車,將壹堆壹堆的雪,用毛驢車運送到村北的大田地裏,這些冬雪,仿佛村裏人儲存了壹冬的希望壹樣,來年會在家鄉耕耘的土地上生根發芽。
如果需要壹種意向的精神支撐,無疑詩歌是最好的橋梁工具。因為在內心的世界裏,永遠捆綁不了詩歌理想和追求。除非把詩歌當成壹種框架,壹種固定模式,但誰也做不到。或者說,做到了,那意義又會在什麽地方。